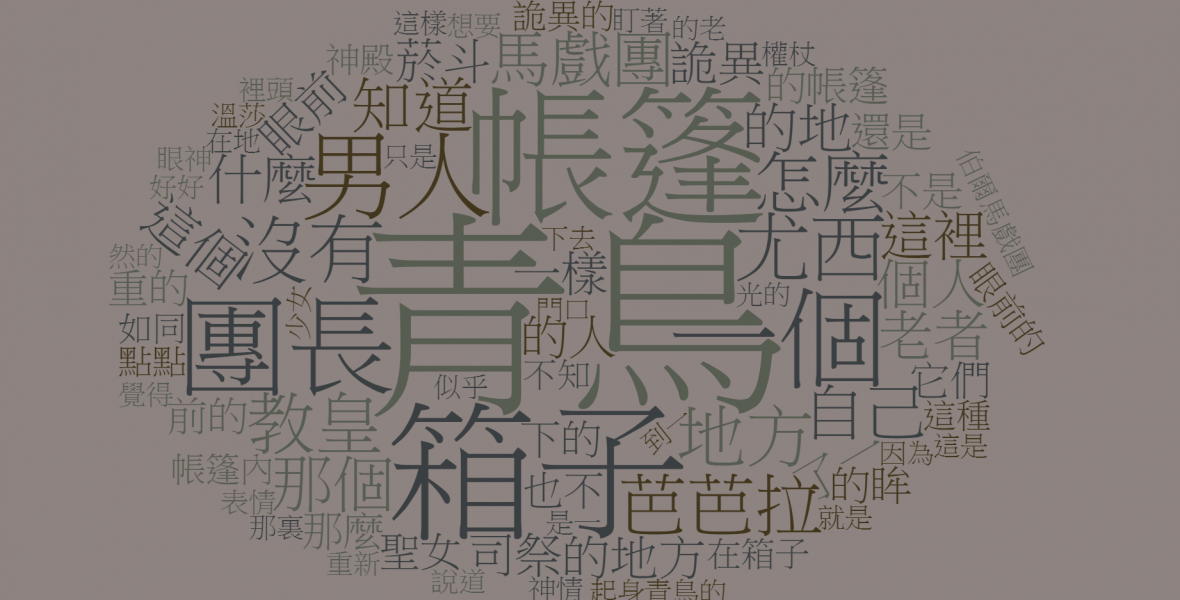 x
x
「唦⋯⋯」
光禿禿的老樹下是成堆的落葉,它們失去了原有的嫩綠跟新鮮,變成乾枯醜陋的褐色落葉,它們將成為世界上最不起眼的存在。就連無家可歸的流浪漢也不願施捨一點目光給予它們,風起它們便被無力的托起,風停它們又搖搖晃晃地落下,重新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孤伶伶的躺在那任由大自然的宰割。
一個存在感如此低薄的地方,卻有一個身型削瘦的黑衣人拖著腳步,停駐在老樹下。
深深凹陷的眼窩下,一個幽黑無光的眸子,那裡頭如同黑洞一樣深不見底,只給人帶來毛骨悚然的詭異感。
「啪喳、啪喳。」黑衣人赤裸的腳無情的碾壓一地的落葉,將它們碾碎。
突然之間,一股大風迎面而來,將黑袍吹得凌亂又響亮。
黑衣人不耐煩地想要擺脫這個隨風舞動的袍子,他臉上顯露出了不耐煩,似乎連同認為這個像是黑魔法巫師的詭異袍子的不滿也宣洩而出,覆蓋在厚到無法辨認原貌濃妝下的面容厭惡的皺。
「青鳥,你在幹嘛呢?」身後走來一人,他是一個面容滄桑的老者,手中顫顫巍巍的拄著拐杖,隨時會跌倒不起的模樣讓人看了都為他捏把冷汗,但此刻青鳥顯然沒有這個心思去理會老者,他臉色明明被白粉塗的蒼白,卻顯得陰沉又喪氣。
「今天有幾個人來看?」沉默良久,青鳥打破寧靜。
「有多少人都隨便吧,不管幾個這個月都要吃土。話說,你怎麼又忘記把頭髮拿下來啦?」老者豪不在乎的聳肩,他走進青鳥,將他的一頭黑髮扯下。
「啊⋯⋯」青鳥手摸摸自己原本的髮絲,心情似乎穩定了一些,他雙手揉捏似的抓住髮尾的兩側,原本附蓋在假髮下的髮絲在月光的照耀下透出青藍色的色澤,隨風飄逸的長髮真的宛如青鳥的尾巴一樣。
老者不知不覺看愣了神,他抹了把滿是皺紋的臉,感嘆的說道:「其實吧⋯⋯在這裡真是糟蹋了你,你應該去那邊的。」
「哪邊?」青鳥眼神茫然的望向老者。
「當然是那兒啊,那裏吃的、穿的都比這裡好上不知多少倍,還不用擔心明天需不需要吃土。」老者理所當然的指向與身後破爛帳篷並排的華麗套組帳篷,那裏頭燈光鮮亮,隱約還聽得見裡頭的歡笑。
青鳥意興闌珊的瞥了一眼老者指向伯爾馬戲團,視線不停留的移向別處,即使在望向燈火通明的不遠處時,他那雙黑洞般的眸子也沒有照映出任何光芒及事物。
「卡芬(coffin)你會想去那裏?那裏有你說的那麼好嗎?」
名為卡芬的老者聞言愣了一下,他盯著青鳥片刻,自嘲的笑道:「好與不好,要去過才能知道。我怕是連進去的機會都沒有。誰叫我是個又老又一無是處的老傢伙呢,連名字都那麼晦氣。」
「是嗎?」青鳥踢了一下腳邊的碎石,他看見卡芬眼中的滄桑,最後還是沒有把心中的話說出來。
其實,比起那種地方,我更喜歡這裡,因為在這裡才有種真實的感覺。看似破舊,卻充滿生機;每天吃土,卻比任何人健康;雖然窄小,卻能剛剛好容納足夠的人數;不明亮,卻有最悅耳的歡笑。這種地方⋯⋯不好嗎?
24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iDQ659ZoGR
24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oF57ubB2xH
「是這裡嗎?」
「就這裡吧。」
「地址是不是有點怪?你確定這裡不是廢墟?」
「旁邊看起來也不像啊?那麼華麗怎麼可能是馬戲團?」
「你沒聽說過那個很有名的伯爾馬戲團嗎?搞不好就是那間啊。」
「睡昏頭啦?再怎麼有名也不過是個馬戲團,能華麗到這種程度嗎?你說這是哪個有錢人金屋藏嬌的地方我還信。」
「好吧好吧,就放這。」
當芭芭拉一睜眼時就發現自己在一個沒有陽光的地方,身體也因為空間限制整個人蜷縮著,也是醒來許久她才意識到自己被關在一個箱子中,正被運往某個未知的地方。
她嘗試對外頭的人求救,因為聽那兩人的對話,他們並不知道箱子裡裝的是一個人,只是意外得到一筆龐大的報酬,想也不想就接下這筆交易。但無論芭芭拉怎麼喊,箱子內就像與外界隔絕一樣,只有芭芭拉急促又大聲的喘息,她知道他們在說什麼,他們卻始終聽不到她的聲音。
「碰──」
箱子被重重的擺到地面上,隨著搖晃一轉,芭芭拉的肩膀撞上箱板,她咬住牙才沒有叫出聲,只是悶哼。
兩個送貨員將東西送達目的地後便迫不及待的回去細數拿到的酬勞,也不在乎箱子究竟會不會有人發現。
芭芭拉絕望的瞪著眼前的黑暗,雙腳早已無力去想辦法脫離箱子,她又會淪落到什麼地方呢?活得下去嗎?還是又要繼續遭到那些恥辱?
她的未來前景就如同眼前的黑暗,無邊無際,充滿了未知,下一步是懸崖還是刀山他一無所知。
不知道的話⋯⋯就走下去吧,走下去就會知道那是一條怎麼樣的路了。霎那,那雙亞麻色的眸中又開始閃耀那抹消逝很久的光芒。
活下去吧,芭芭拉。
24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l9smrLac5l
24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c2e7OQXjh0
神殿在白日擁有最美的陽光落下,柔和的光芒與大理石地板融為一體,更為沐浴其中人添增一層柔光。
一名身披單薄白袍的中年男子以跪坐的姿態靜靜在神殿正中央,他面色平靜,面容有種渾然天成的慈祥寧靜,白中帶金色的長髮平直的被順在背後,髮尾被一條麻繩束起。
這幅靜止的畫面持續了很久,彷彿過了數年一般。
男人微微張開眸子,那是一雙溫潤的咖啡色眼眸,但其中卻參雜著火焰似的紅光。
「若昂(João)⋯⋯」他輕聲的呼喚回盪在神殿中,語句停頓似乎希望呼喚的人能夠回應他,但只有空蕩蕩的回音。
「你想要的,我一定會幫你達成。」垂在身側的雙手緊緊握起,那般的用力跟男人本身的柔弱形成對比。
男人眼神空洞的望著前方,他身軀不自覺得像前彎,貪戀著眼前不存在的事物,脖頸隨著動作而向上仰,眼簾半垂。
「叮呤──」輕脆的鈴鐺聲如同命運的鐘聲,在剎那將男人打回原位,男人如夢初醒,身體一顫,側眼看去,平擺在地的權杖因為剛才的動作而滾動,看到那個由金線刻畫圖騰,男人眼中的火光消散無蹤。神色隨著男人起身,一點一點得逐漸黯然。
「唦⋯⋯」男人披上被擺放在一旁華美高貴的聖袍,厚重的衣袍如同將無形的重量化為實質,重重壓在肩上。男人姿態緩慢的將高冠戴在頭上,重量又再增添幾分。最後,他拿起沉重的權杖,優雅、緩慢的朝神殿外走去。
出了神殿,馬上有位小司祭恭敬又快速的上前,接過男人手上的權杖,並跟隨其後,一邊詢問道:「陛下今日是否要去見聖女殿下?昨日聖女殿下的覲見請求⋯⋯」
「近日應是沒有大事,聖女又為何求見?」教皇面色淡淡,看不出真正的心情如何。
「聖女殿下說是有關溫莎公爵大人的事。」說著,小司祭面上也露出困惑的神情,似乎不明白足不出戶的聖女為何會跟溫莎公爵有所牽扯。
教皇內心輕呵一聲,面上莊嚴的說道:「這並不什麼重要之事,駁回吧,讓聖女別小題大作。」
小司祭聽得一頭霧水,卻還是應下,拿著權杖先行告退。
教皇獨自回到辦公處,摘下繁重的高冠,他按下呼叫鈴,沒過片刻,一名穿著與普通司祭不同的司祭敲門入內,他這種穿著是隸屬於教皇底下的司祭,只聽命於教皇的命令。
「事物可辦妥?」教皇一邊批準一些需要教皇審核才能通過的公文。
「一切都遵照陛下的命令執行,具回報,已如實將東西送達伯爾馬戲團。」
「好,可以退下了。」教皇點點頭。
待司祭離開,教皇才停下手邊的工作,他將身軀倚靠在椅背上,神情向著前方發愣。
米格爾身邊可不能再有變數出現,這樣就壞了一切的平衡,不過也剛好,具回報米格爾異常的珍惜那個人,那如果把那個人送到伯爾馬戲團那種有趣的地方,等他去時,是不是也算收到一份大驚喜呢?
想著,教皇勾起滿意的笑容,心情愉悅卻又病態。
米格爾 ‧ 溫莎,你就好好接受我給你的大禮吧。要怪,就怪你要生在溫莎這個家族,又偏偏是那個人的兒子⋯⋯
24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VHzLDwW8Pw
24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No36EQ1qJ3
夜色漸深,點著暗黃燈的帳篷內,一名身穿舊時代軍裝的中年男子一手摩梭著他的絡腮鬍,另一手不安分的擺弄手中被捏爛的信封,連腳也不閒著,不停的抖著。
男人高聳著眉梢,啣在嘴邊菸斗隨時會掉到地上,桌邊黃燈微弱的光照亮帳篷內,帳篷內沒有什麼稀奇古玩,卻像軍糧庫一樣,亂中有序的擺放著各種糧食,那種仗勢像是隨時會戰爭饑荒一樣。
詭異的服裝、詭異的行為、詭異的男人、詭異的帳篷。
就當男人享受著詭異的生活時,被外頭闖入的人硬生生打斷。
來人扯開帳篷帆布,朝男人大吼:「你是不是又再抽菸了!」
團長一個激凌,菸斗就這麼掉落在地。
「怎啦!?」團長語氣不善的瞪著身穿白袍的來人,一邊手腳僵硬的彎腰撿掉在地上的菸斗。
來人掃了一圈堆滿食物的糧倉──團長帳篷,眼鏡下的雙眸瞇成一條直線。
「你是活得不耐煩嗎?怕死的存了那麼多糧食,結果肺先壞死,簡直愚蠢。不過這樣也好,放心吧,等你死了,食物我會好好幫你保管的。」
團長不滿的想瞪自己的主治醫生同時也是馬戲團的重要人物,卻在他冷漠高壓的眼神下敗下陣來。
「嘖,不就是菸嗎,我當然可以不抽!」團長忍著內心的吶喊跟痛苦,面上瀟灑的把菸斗丟置角落,將顫抖又脆弱的手隱藏到桌面底下。
「你做了明智的選擇。」醫生推了推眼鏡框,扯出一抹微笑。
「我的菸斗⋯⋯咳,不說這個。尤西,你應該不是只為了這件事來吧?」尤西平時都只對他有興趣事付出行動,若是只是抽菸這種小事他根本不屑理會團長。
「那個啊,我差點忘了,是青鳥在門口收到一份大包裹,他正準備搬來給你。」
「你一向對青鳥的事情那麼上心⋯⋯」團長嘟嚷一句,馬上回道:「等等,門口?」馬戲團並沒有所謂的門口這種東西。
尤西也意識到這句話的問題:「就是⋯⋯大馬路前的那塊空地。這不是重點,你帳篷那麼亂,那個大箱子肯定擺不下,快騰出一個位子吧。」
團長揉搓著頰側的鬍子,表情凝重的搖搖頭:「不,我相信青鳥能夠好好保管這個包裹,怎麼處理就交給他吧。」
但實際上,團長這凝重的表情背後目的卻是來自於團長個人小小的私欲。
咱們馬戲團從創始就從沒有收過什麼好包裹,再說,我的帳篷這麼神聖的地方怎麼能放如此龐大的障礙物?這裡只容納的下食物跟菸斗。
「好的,我會轉告青鳥。」尤西似是早知道團長會這樣說,他點點頭,就用飛快的速度離開團長帳篷。
等尤西離開,團長才鬆了口氣,以最快的速度從角落撿回被牠丟棄的菸斗,心疼仔細的擦拭後又重新開始煙霧瀰漫的極樂世界。
24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UCbQ90F1v6
24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hWmqRlQMFA
另一個帳篷內,格局比團長的帳篷略小幾分,裡頭卻空如沒人住的帳篷。
一張床、一張桌、一張椅、一個衣櫃,以及由一個帆布隔開的浴室,這就是青鳥的帳篷擺設。
「怎麼打開⋯⋯?」青鳥跪坐在箱子前,眼神認真又困惑。
「算了,搬去給團長吧。」他放棄研究這個他剛才不小心失手砸在地上也毫無破損的箱子。
「嗨,小青鳥。」帳篷門口,尤西自在如進家的踏入,看著青鳥面無表情轉過來的模樣,他忍不住伸手搓揉青鳥美麗的髮絲。
「別碰。」青鳥皺了皺眉,卻沒有劇烈的反抗,只是站起身表達自己的不滿:「我要搬去給團長。」
「他說全部交給你處裡,不用搬去給他。」尤西咧嘴說道。
「這樣啊⋯⋯」青鳥點點頭,又重新跪坐在箱子前,盯著箱子發呆。
「你怎麼就盯著箱子發呆?不開嗎?我可以借你鋸子。」尤西盯著青鳥的反映,越看越覺得有趣。
「打不開。」青鳥搖搖頭,他站起身,把尤西推出帳篷。
尤西還沒反應過來,就被不可反抗的強大蠻力給推出帳篷,他怪罪的看著站在帳篷口,神情憔悴的青鳥。看似這麼瘦弱的人,力氣到底怎麼來的?
青鳥趕走尤西後又重新坐回箱子前,他手輕輕敲了敲箱子,見還是沒反應,他下巴靠在箱子上,神情苦惱:「如果打不開,裡面的人會不會死?」
他在看到那箱子的第一刻,就知道裡頭裝著一個人,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知道,但回神時,他自己已經將箱子搬回帳篷內。
正苦惱著,青鳥將手擺放在箱子上平貼,就在霎那,箱子跟青鳥手掌的貼合處浮起點點藍光,就像飄起的藍色雪花一樣,飄盪在帳篷之中。
「這是?」青鳥望著這些光點,面色茫然。
光點越來越多,將昏暗帳篷的每個角落點亮,如同身置幻境一樣,美的夢幻。
「唦──」一個解體的聲音,箱子在瞬間化為烏有,飄散成點點光輝。
青鳥幽黑的眸被照映成耀眼的青藍色,消散的箱子中央出現一個蜷縮的少女,她沉沉的睡著,睡在由光點織成的小窩中。
「好美⋯⋯」青鳥一向面無表情的臉浮現出紅暈,無精打采的眸也被點亮,他身體向前傾,想要更靠近那個美麗的少女。
而沉睡的芭芭拉也在箱子解開的同時感到前所未有的解放跟舒暢,她想要好好的伸展僵硬的身軀,就在睜眼的同時,她看見了一雙閃閃發光的眸。
「這是哪⋯⋯?」芭芭拉全身痠疼得厲害,卻還是強撐著起身,她與眼前的人平視,對於眼前美輪美奐的場景不自覺得感嘆,說不定,自己這是來到天堂安息了?
面對眼前的少女,青鳥一時發愣,沒聽見少女說什麼,他張了張嘴,乾巴巴的問道:「妳叫什麼名字?我是青鳥。」
芭芭拉覺得眼前的場景似曾相似,卻又說不出個感覺,她想起那個自己所背負的代號,輕輕說道:「芭芭拉,是我的名字。」
ns18.189.1.87d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