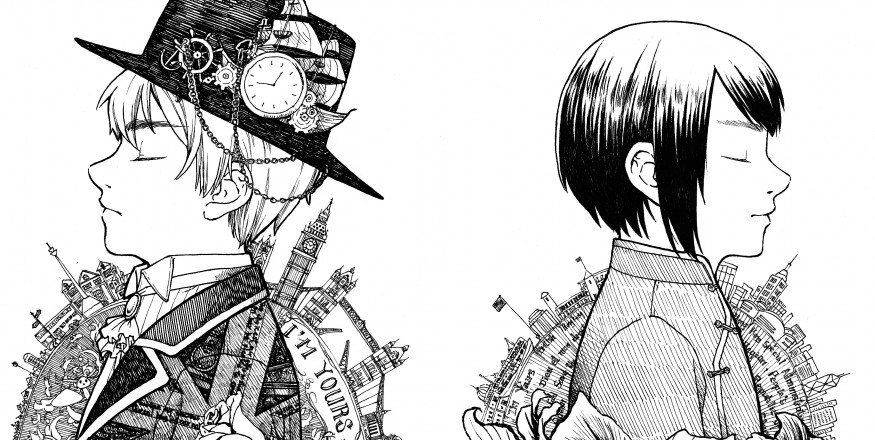二零一四年六月,蘇格蘭。
我很怕跟家人獨處。
「你這傢伙……」
因為我與家人的關係很差。
「我不是叫你這傢伙別再來找我嗎?亞瑟。」
當我的哥哥──蘇.格.蘭購物後回家,發現我獨自站在他家前的圍欄外時,他露出一張如同看到了一個欠債卻不還錢,如今還要來多借一點的「朋友」般,厭惡及煩躁表露無遺。
我知道讓他如此討厭我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長得一點也不像,特別是他的棕紅色短髮及深邃的綠色眸子,每次看到它們時我都會感受到我與他之間的距離到底有多遙遠。我們唯一的相同之處大概就只有「柯克蘭」這個姓氏,但是即使「姓氏」是一樣的,我們之間的關係還是從沒好過,只因某些事──第二個原因──並非只要有「血緣」關係就能利用時間解決的。
那是比一戰 更為遠久的事,遠久得早就被千千萬萬的民眾忘記,遠久得早於和平的世界中失去蹤影,因此,雖然我知道原因,但我還是無法理解為何過去的事到了現在依然影響著我倆的關係,甚至迫使他要做出離開這個家──「獨立」的決定……
啊,知道與理解是兩碼子的事。
不過,假如他不做出這樣的決定,我也不會頻繁地在他的家門前,等待著總是晚歸的他,問著同一條我早就知道答案,卻不得不問的問題:
「你……你仍然想離開這個家嗎?」
事實上,我會這樣做單純是因為女王的命令──對,是女王的命令我才會這樣做,否則我才不想為這個哥哥多費氣力。不過,正正因為我最近幾乎每天都這樣做,所以我比以往知道了更多住在這裡的人民的想法及特質,也知道了很多關於哥哥的事,以及他鮮為人知的溫柔一面。但是我──女王最終想靠著這些行動來換取的結果,卻是一個即使我知道了這些事情都無法得到改變、只能成為妄想的結果。
我曾經告訴女王這一切都將會是徒勞,因為哥哥很倔強,對任何事情都很堅持,但親愛的女王卻回答:「只要我想到或許有一天,小蘇的心情突然變好,懷著笑容回答你:「我不想離開了。」、「我想留在這個家。」時,我就覺得你應該要一直問下去,問到他感到厭倦也繼續問下去啊。」
啊啊……但是,即使我──女王懷有這種決心,我們都知道自己能問這條問題的時間只剩下少於三個月了。而今天的哥哥就跟平常一樣回答道:「對,我從未改變過這個想法。」
果然如此。我聳肩,轉身,留下一句「我明天會再來。」後便開始往自己的家步去,可是在我離開哥哥的視線範圍前,他卻叫住了我,語氣相當惡劣,猶如想殺了我般:
「Arthur.(亞瑟。)」
我停了下來,回頭看他:「What?(什麼?)」
「別再來了。」他的眼睛閃出致命的綠光,幾乎讓我發抖:「我不認為我們之間還有話可說。」
這傢伙難道以為我是自願到這裡來找他的嗎?「我……我來這裡是因為女王的命令,並不是我真的想來這裡,請你不要誤會啊!笨蛋。」
「如果是這樣就最好了。」他冷淡地道:「我不希望明天的這個時間,我還會在這裡見到你。」
真的如此討厭我嗎?啊,好吧。
我冷笑一聲,往他身邊走去:「你真是一個笨蛋啊,哥哥。『獨立』對你來說有什麼好處?」
「哦?」他輕笑,雙手捧著一堆用紙袋裝著的麫包及蔬果,那份量多得我認為單單利用一人之力是無法捧著的,可是他輕易而舉地做到,有如某個笨蛋。他捧著那些,輕鬆地走過我剛才站著的位置,努力地空出一隻手來從衣袋中取出鑰匙,把圍欄打開,步進種滿了薊花[1]的前園。他道:
「我沒有失憶啊,亞瑟。我不會忘記阿爾弗雷德。」
我愕視他,馬上感到自己被侮辱,但我沒有讓這感受化為憤怒。相反,我很快地冷靜過來,理性地回應:「但你的情況跟那笨蛋不一樣,而我的情況也跟當年不一樣了。我改變了。」
「有什麼不同?同居的時間長短?還是髮色的差異?」他嗤之以鼻,不把我的話聽進耳內:「而你又改變了什麼?我可是覺得你跟以往一樣。」
話後,他辛苦地一邊捧著東西,一邊替換手上的鑰匙並把下一道門打開,可是這一次,由於他的雙臂實在捧著太多東西,結果他迫不得已地先把它們放在地上,並於開門後拾回。
在期間,我跟著他一起步入前園,同時回答他的諷刺:「不管是同居的時間,還是髮色的差異都不是我們要談論的重點吧?哥哥。至於我到底有什麼改變?我深信你很清楚吧?」
他笑了:「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真是麻煩的哥哥。「答案就在眼前。我不認為這是你要問的問題。相反,你應該問問我們之間到底有什麼要保留的。你的情況你自己很清楚。各大社會及經濟學家已有一堆論文分析了利與弊,我就不重覆了。但我在這裡還是有件事要你清楚知道──」
「我不認為我們之間擁有『需要共同保留』的東西呢。」他推門進去,似乎想單方面地終結話題,於是我在他要走進屋內前說出被打斷了的話:
「那麼,我們都尊重的女王陛下呢?」
他開門的動作有著明顯的停頓,這句話似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我不清楚這個作用對現在的他來說究竟是好還是壞,因為他很快就恢復動作,毫不留情地說了一句「你還未有威脅我的資格。」後便走進了進去,用力地把門關掉了。關門時的力度比想像中還要大,那吹來的風猶如摑了我的臉一巴,令我的身體和心靈都被刺痛。
威脅。
這是威脅嗎?
別開玩笑了。我從來都沒有借用女王的名義來威脅任何人。我這樣做的目的,只因為女王陛下真的不希望你離開,而我不希望她為了你這個笨蛋而流下任何一滴眼淚罷了。
然而,你卻說我是在威脅你嗎?
你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感情對你的弟弟說出這樣子的話來?
別開玩笑了,你這個任性的笨蛋。
所以我才這麼害怕跟家人獨處。
我吸了口氣,決定向那道總是分隔我和哥哥的門道:
「不管是笨蛋阿爾,還是那個孩子,都知道我不是會借用女王的名義來威脅他人的人。我希望你能重新思考自己到底說出了什麼樣的話,也希望你為這件事向我道歉。再見了。我明天會再來。」話畢,我離開,走出那遍種滿了薊花的前園,沒有猶豫地往回家的路走去,感受著夏天的夜晚以及這個國家的寧靜,可是我心中的憤怒依然沒有消失。
啊,很久沒有這麼生氣了。
上一次是為了什麼而生氣?說實話我已經忘記了,但我記得自己最生氣的那一次是為了什麼:
賀瑞斯。
那一次是我與那孩子將要分開的年頭。我因為覺得自己被上司騙了而生了很久的氣,氣他一直把我從那孩子的身邊叫走,氣自己沒有發現到原來自己與那孩子的緣分快要走到盡頭。結果,回過神來的時候已經太遲,最後還必須勞煩到柏藤先生才可以收拾殘局,為那個孩子的未來設下最低限度的「民主」保障。雖然我到了現在仍未知道自己當時的「臨急抱佛腳」對他來說是否一件好事,但我從沒有為自己所做的而感到後悔,因為我確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好的──
「不管是笨蛋阿爾,還是那個孩子,」我突然憶起了自己剛才說的話:
「都知道我不是會借用女王的名義來威脅他人的人。」
接著我才發現到,原來自己在自打嘴巴。
明明為賀瑞斯的事生氣時,我從來都沒有把「女王」的名字掛在嘴邊,也從來都沒有聽從過女王的命令做事,甚至曾經違命,只顧自己的想法而和柏藤先生一起工作。可是,這一次我卻搬出了「女王」的名號……
「我……我來這裡是因為女王的命令,並不是我真的想來這裡,請你不要誤會啊!」
雖然我的確是聽從女王的命令行動,可是我不是機械人,亦不是乖巧的孩子。我絕對懂得分辨是非,亦絕對可以跟隨自己的想法行事,所以假如當時的我沒有搬出女王的名號,那現在的我也不應該搬出她的名號。
如果我現在卻這樣做的話,那我與那個只會聽從上司命令行事,接著不自覺地把自己做錯的一切都推給上司的王耀有什麼差別呢?
「你還未有威脅我的資格。」
啊。原來要道歉的,是我才對。
但是啊,哥哥。
我走到巴士站時停了下來,一邊等待著公車,一邊注視頭上的月亮,為總是「獨立」的「它」感到厭惡,為這個麻煩的「存在」感到了恨意:
「那個孩子可是對著那樣子的傢伙,都依然未想過獨立啊,哥哥。」
我不禁向「它」說道,同時憶起了柏藤先生從香港回來後,他所見到的事實,以及那個孩子希望柏藤先生向我轉述的謊言:
「請告訴那個人,我現在依然活得好好。」
六月十六日,中國總理到訪我國,藉著與我方簽署多份總值逾二千三百億港元的經濟協議之際,要求我們再簽署一份中英聯合聲明成果文件,並同意現時香港的一國兩制方針運作良好。
然而,既然任誰都知道那是謊言,又怎可能會願意簽署?
包括我的上司在內,也無一願意。
[1]薊花,蘇格蘭國花,花語是「嚴格」。蘇格蘭亦有一種名為「薊花勳章」的勳章,是授予蘇格蘭騎士的一種勳章,勳章的格言是:「犯我者必受懲。」
ns3.17.139.45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