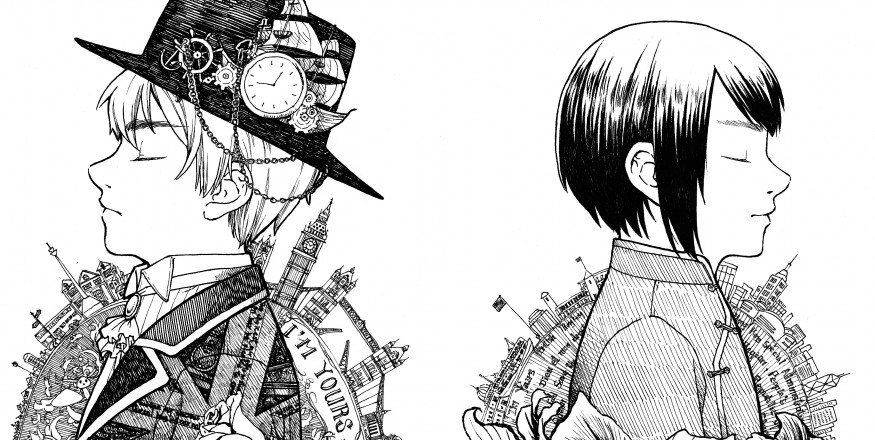二零一四年六月,香港。
我很怕跟先生獨處。
「歡迎光臨!兩位埋面坐啊!(歡迎光臨,兩位客人坐在裡面吧!)」茶樓的侍應高聲叫道後,我與總是穿著紅色馬褂的先生一起坐到一張接近牆邊的四人圓桌旁。侍應隨即帶著一壺水放在我們桌面,替我們開了一張將會蓋滿印章的白色咭紙──點心咭,並且詢問我們要喝什麼茶。
先生沒有猶豫地以普通話回答:「普洱就可以了。」
侍應看了我一眼後,見我沒有意見就轉身離開了。我拉開椅子,待先生坐下後才坐下,整個過程我盡可能表現得自然,不讓先生發現我是故意坐在他的對面,而非旁邊。
坐下後我們沒有馬上交談。先生首先用紙巾抹乾淨所有將要用的碗及杯子,接著是匙和筷子。他沒有清洗餐具的習慣,一直以來都只是用紙巾抹一抹就算了,好像覺得餐具本來都是乾淨般,對這些小節的衛生沒有特別講究。
有時候我會想,如果我小時候沒有跟那個人一起生活過的話,應該也會跟先生一樣不苟小節,也會比較理解先生為何總會想灣承認他是自己的親人。不過,現在的我沒有希望這些事會變成真實的念頭,也不希望這些會變成真實的:我頗為喜歡會苟泥於這些小節的自己。
於是,就在侍應端來茶的時候,我倒茶在自己的碗子上,開始清洗自己的餐具。
先生在此時拿起了一枝筆及一張點餐紙,一邊點餐一邊問道:
「數月不見,你最近過得怎樣了啊阿魯?」
「不錯。」我隨便道,說話時沒有想過此話的真偽,卻為先生所說的「數月」感到驚訝:原來上次見面已經是三月的事情了嗎?時間過得太快了吧?
他又問:「灣呢?她還好嗎阿魯?」
我頓了一下,然後繼續清洗,回答:「我不知道啊。你為什麼不親自去問問她呢?」
事實上,我上星期才到她的家跟她見面,所以基本的事情我還是知道的:她的想法、感受……甚至傷勢等我都在上次的見面看得一清二楚。雖然她請了我喝珍珠奶茶,但事實上她不認為她的反抗已經完全成功。她知道她上司的慾望沒有因為上次的事件而被磨滅,因此她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準備應付將會於未來發生的麻煩事。不過,當我問她會否討厭先生時,她卻沒有作出正面回應,只是給了我一個微笑,說出了一件我相當認同、但渴望去改變的事:
「小香,老師太乖巧了,所以他不會做錯事,也無法做錯事。做錯的,永遠都是人。」
啊。我為能夠明白此話,但依然害怕跟先生獨處的自己感到悲哀。
我完成清潔後把污水倒進大碗裡。先生把筆和點餐紙交到我手上後又道,字裡行間有莫名的傷感:「我之前一直都有找她,可是她不是拒絕接聽電話,就是對著話筒大吵大鬧後就掛線,我到她家找她但她不出現,我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啊阿魯。」
我在點餐紙上畫了自己想吃的東西後,確認我們總共點了八樣東西後便揚手呼喚侍應。其中一個穿著紅色制服的女侍應看到我後找了一個穿黑色制服的男侍應過來。我把紙遞給他後他檢查了一遍,向我確認點餐的數目後便離開。我回到剛才跟先生談話的內容裡:
「其實當時機來到時你和她還是必須見面,你應該不用著急吧?先生。」
他喝了口茶,嘆了口氣:「面對像是阿爾弗雷德之類的外人時我還沉得住氣,但是家人生我的氣時我就無法不介懷,亦無法不著急了。你明白這感受吧?小香。」
我想提出自己的經歷讓我不知道什麼才是「外人」,什麼才是「家人」,不過想到提出對於這次的交談沒有任何益處,於是我把話吞回肚子裡,道:
「如果真的是家人就必定會有原諒對方的一天。我想你還是讓時間沖淡一切就好了。」
「你說得對啊阿魯。家人就是有這樣子的方便啊阿魯。」他點點頭道:「外人的話,不管是朋友還是你的愛人,只要他是外人就永遠都敵不過時間,因為時間會沖淡一切,包括感情啊阿魯。」
外人和時間。
突然之間,我覺得此話充滿了尖刺,而那些尖刺剛好刺中了我心中那永遠無法癒合的傷口,使我的心隱隱作痛。我想起了某個身影。
「但如果是家人的話就不同了阿魯。血緣會讓你們永遠連在一起,因此對家人來說最大的麻煩就是衝突,而時間就是衝突的最有效良藥啊阿魯。」
我收起心中的痛,在仔細聆聽他的話後不禁回應:「先生,你在自打嘴巴啊。」
他又嘆了氣,無力地半躺在仍未上菜的圓桌上,一臉不安地回答:
「但是知道與理解是兩碼子的事啊,小香。」
我愣住,覺得話中有話,卻毫無頭緒:「先生,你想說什麼?」
他沉默半晌,回到坐姿,拾起了自己的茶後閉上了雙眼,接著徐徐喝下,直接將茶完全喝光才放下茶,帶同不苛言笑的態度回答我的問題:
「上司知道了。」
我的世界失去了時間似的靜止著:不管是正在捧餐的女侍應,還是坐在周圍的客人都沒有一個能夠發出我在此刻可以聽見的聲音。我此刻唯一聽得見的,就只有自己的驚呼:
「Pardon?(請再說一次?)」
他盯緊我道:「你與那個男人見面的事,傳到我的上司耳邊了啊阿魯。」
那個男人是指彭先生。我的理智分析出這個答案,但我想不透為何會洩漏了風聲:我和我的上司不一樣,只住在一間小小的公屋,也沒有「保安」或「保鏢」──不。保安的話,每棟公屋的大堂都會有一個……但是我跟那位保安先生不認識。再者,就算他認識彭先生,他又怎會想到他是和我見面──
「別猜了啊阿魯。我也不知道他為何會知道啊阿魯。」 先生打斷我的思路道,令我不自覺地把原本因為思考而不禁低下了的頭抬起,看往一臉憂愁的他正倒茶給自己:
「不過,既然他知道了我也無法裝著什麼都看不見,所以我今天才會約你來茶樓啊阿魯。」
我有將要被訓話的預感。
「先生早就知道了?我與彭先生見面的事。」我問。
他用複雜的眼神凝視我,那有如責備亦有如擔憂。我不知道哪一個才是正確答案,但不管答案是什麼,我也不認為它有助我結束這場飯前的對話。他嘆了口氣,又喝了口茶後回答:
「不是啊阿魯。是上司讓我來責罵你我才知道的。」 他道:「告訴我你們談了什麼吧阿魯。」
「彭先生只是來探望我……」我馬上澄清:「作為朋友。」
「朋友嗎阿魯?」先生揚起一道眉:「真的跟那個人沒有任何關係嗎阿魯?」
那個人。
這一次我呆了足足半秒鐘才懂得反應,為自己立即明白先生所提及的那個人是誰而煩躁不安:
不能給他添麻煩了。
「與那個人沒有關係。」我說謊。
「是嗎阿魯?」他聽見後好像鬆了一口氣似的微笑,又喝了一杯茶:「那就好了阿魯。你知道他為了此事吵了多久嗎?吵得我的白頭髮都變多了啊阿魯!」
我附和他微笑,喝了一口茶,真心希望他是真的相信我的謊言──
「但是啊,小香。」
可是,開心的時間總是過得特別快:就在我這樣想的瞬間,先生說了一些話讓我的動作止住了。他的話打破了我的期望,打壞了我與他的關係,讓我為自己的未來感到了迷惘。有時候我會因為這樣的話語而感到悲哀,覺得先生早就不把我當作親人,只把我當作玩偶。但是,當我想到他所經歷的一直都比我多,他所承受的痛苦亦比任何人多,我就無法說出任何話去反駁了。他道:
「我說如果啊阿魯。如果你想離開我到外人的身邊,我可是會很頭疼的啊阿魯:不管是因為你一直在籌備的『佔中』,還是因為我的上司也會讓我頭疼啊阿魯。你明白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嗎?」
聽到「佔中」這個詞彙時我呆住了。我沒想到這件由上年起就一直籌辦到現在的活動會引起了先生的關注。我明白那件事的目的是什麼,也明白它有何意義,更明白它開始了後會對我的錢包造成多大的負擔,但是我從未反對過這件事──不對。在我的立場上我是無法反對的。人民的心意構成了我們,這意味著我們本來就代表著人民,所以我根本無法發出任何聲音。一直以來,我只能依照人民的想法思考,卻聽從上司的指示做事……
欸?這原來就是一直以來的我嗎?
原來我一直以來都沒有自己的立場嗎?
原來我一直……跟先生一樣嗎?
啊。所以我才從未想過要離開先生,只想過從他的手上得到更多的自由吧?不過即使把這些話告訴了先生,先生也會把它詮釋為另一種不悅耳的語言吧?就好像他不喜歡「佔中」這件事,也不喜歡我跟那個人聯絡般。在他的眼中,這些都是背叛的行為,是我不應該做的。
而面對態度總是如此強硬的先生──不。是他的上司。
面對態度總是如此強硬的上司,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做事,讓他從中看到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令他明白到我真正的想法,並希望我的行動可以感動到他:
有時候,沉默不語的態度會比起冠冕堂皇的藉口還要好……
這樣想道時我點頭說我知道。一個捧著很多籠點心的女侍應此時走來,我與先生不約而同地將背部貼近椅背,方便她上菜:「蝦餃、燒賣、叉燒包。靚仔,俾張咭黎。(帥哥,給我點心咭。)」
我把點心咭遞給她,她分別在中點和大點之間的欄位蓋了三個印章,接著便捧著其餘的點心到別的地方。我把咭收回來,放在點心紙的旁邊後打算繼續剛才的話題,但先生已經舉起了雙筷,一邊向我微笑,一邊溫柔地叫我趁熱吃,有如被打斷說話前的先生根本不是他。
我不禁嘆了口氣,舉筷,夾起了一顆蝦餃,將它塞進嘴裡。
先生吞下一顆燒賣後道:「我們來談些高興的事吧阿魯。」
我再一次附和他微笑,點頭說了聲好,從未正面回應過他的話語。我只是默默地吃,有如我一直都默默地做事,默默地發起諮詢,默默地發起投票:
六月二十二日,由「佔中」發起的民間全民投票正式開始。
投票的內容為:「我的未來應以何種方式決定?」[1]
259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9EuW6w1Yst
[1]622民間全民投票,簡稱622公投,由「佔中」發起,為促進真普選而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舉辦的一次民間全民投票,選出一個行政長官選舉方案。此投票要求市民在真普選聯盟方案、人民力量方案及學界方案三個政改方案中作出選擇,得票最 高的方案,將成為佔中運動行動支持及推動的方案。259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OoKSQWK4V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