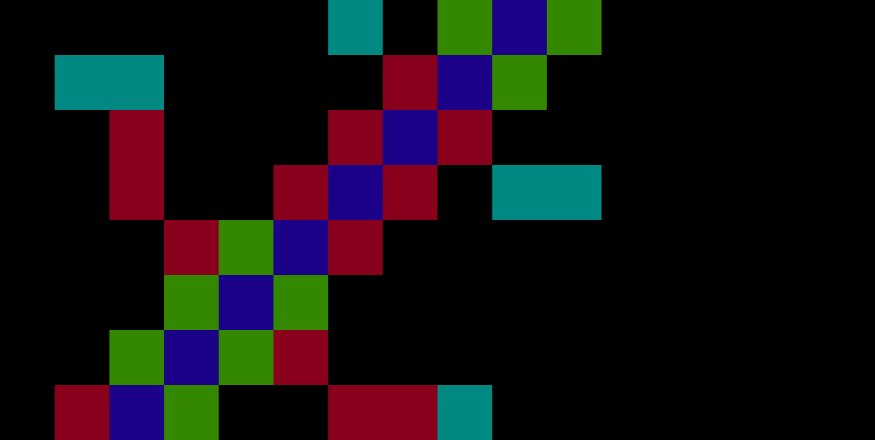莉莉絲癱在稻草堆上,渾身顫抖,喘息聲在空蕩的地下室裡回蕩。阿爾弗雷德的屍體倒在她面前,鮮血染紅了稻草與石板,淨化之劍還插在他的胸膛上,劍柄微微晃動。她腦子一片空白,視線模糊,黑暗氣息散去後的冰冷像潮水淹沒她的意識。她的腿軟得像棉花,眼皮沉重得抬不起來,終於,她頭一歪,完全昏死過去,身體無力地滑進稻草堆,翅膀壓在身下,像一團破布。
在她昏迷的黑暗中,一陣猥瑣的怪笑響起。一個身影出現在地下室中央,披著破斗篷,滿臉痘痘,眼睛眯成一條縫,笑得像個偷窺狂,手裡拿著根歪歪扭扭的木杖。他咧嘴道:「哎呀,我的小魅魔,玩得太嗨了吧?瞧這亂七八糟的!」莉莉絲毫無反應,昏迷得像塊石頭。
他搖搖頭,自顧自嘀咕:「這可不行,遊戲角色可不能崩成這樣呀,得好好修修」
他一揮木杖,一股熱流從她頭頂灌入,像熔岩順著脊椎流向下身。她的手腕與脖頸傳來刺痛,聖光枷鎖「咔嗒」裂開,碎片散落一地,勒痕卻還留在皮膚上。熱流在她腹部聚集,隨後向下身湧去,一陣光芒自莉莉絲內部炸開,像有什麼在重塑她的血肉。內臟的撕裂與外傷逐漸消失,可最後故意留一手,自然癒合產生的瘀青與翅膀的殘破被刻意保留,和勒痕一起像個嘲諷的印記。他嘿嘿一笑,自言自語道:「給你恢復出廠設置,夠意思吧?這下可得好好玩,別又搞砸了。」
修復完畢的瞬間,莉莉絲猛地睜開眼,頭痛欲裂,喉嚨乾得像燒著一樣。她喘著粗氣,茫然地看著那個猥瑣的身影。他蹲下來,湊近她的臉,咧嘴說:「醒啦?動作挺快嘛。」她想動,可四肢還像灌了鉛,只能瞪著他,眼神混亂。他拍拍手,站起身,嘀咕道:「這次算你運氣好,碰上我心情不錯。」然後他轉身,丟下一句:「小心點啊,別又把自己玩崩了,這次我還能補償你,下次可不一定,記住小命可就這一條!」語氣裡帶著嘲弄與警告,隨後身影一閃,消失在空氣中,像從沒出現過。
莉莉絲呆呆地看著他離去的地方,腦子一片混亂,不知道這「補償」意味著什麼。她摸了摸手腕,枷鎖已不見,只剩勒痕隱隱作痛。她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身體,沒感覺到什麼顯著變化,只是疲憊似乎減輕了些。她喘著粗氣,拖著虛弱的身體爬起來,踉蹌走向門口,尾巴拖在地上,翅膀無力地垂著,身上滿是瘀青與汗水。她走出不知為何敞開的鐵門,冰冷的夜風吹過她的臉,帶來一絲清醒。她沒回頭,跌跌撞撞地逃進無邊的夜色。
幾天後,她流浪到一片荒涼的森林。樹木枯瘦,枝丫像爪子伸向天空,地上覆著厚厚的落葉,踩上去發出脆響。她衣衫襤褸,破布勉強遮住胸口與下身,眼神空洞,像個行屍走肉。饑餓啃噬著她的胃,她試著抓樹根下的蟲子吃,手指顫抖著挖開泥土,可最後還是不敢真吃不下去。她靠著一棵樹坐下,氣息微弱,意識模糊,感覺自己隨時會倒下,再也爬不起來。
一個少年發現了她。他叫艾倫,皮膚曬得黝黑,手上滿是勞作的繭子,穿著粗布衣,肩上扛著一把柴刀。他看著這個長著翅膀的女人,沒問她的來歷,只是蹲下來,遞給她一塊硬邦邦的黑麵包。「餓了吧?吃點。」他說得簡單,聲音粗糙卻溫暖,像夏天的土路。
莉莉絲接過麵包,機械地咬了一口。麵包硬得像石頭,硌得她牙疼,可她還是嚥下去,胃裡一陣翻騰。她抬頭看他,眼神空洞,沒說話。艾倫也不多問,坐在她旁邊,開始削一根木頭,刀刃刮過木屑的聲音在寂靜的森林裡顯得格外清晰。過了一會,他又掏出一小塊風乾肉,撕成兩半,遞給她一半。她接過,慢慢嚼著,腥味在嘴裡散開,讓她回億起地下室的交易,低頭繼續吃。
接下來的日子,艾倫每天都來。他帶著食物,有時是黑麵包,有時是煮過的根莖,偶爾還有從村裡偷來的半個蘋果。他不問她的過去,只是陪她坐著,聊些村裡的瑣事——誰家的牛跑了,誰又摔進了河裡。他的話不多,卻像溪流,緩緩流過她冰冷的心。她起初沉默,像塊石頭,可慢慢地,他的單純讓她緊繃的神經鬆了一絲。她開始回幾句話,聲音沙啞,像從沒用過的舊琴弦。
艾倫為她搭了個小屋,簡陋得像個鳥窩。她搬進去那天,他扛來一捆乾草,鋪在地上當床。她躺上去,聞著乾草的清香,與地下室的"血稻草"完全不同。她醒來時,發現艾倫坐在門口削木頭,手邊放著一碗熱氣騰騰的野菜湯。她接過碗,喝了一口,溫熱的湯汁順著喉嚨滑下,讓她空洞的眼神亮了一瞬。
兩人開始一起生活。她學著種菜,手指被泥土磨得粗糙;他教她劈柴,斧頭在她手裡顫抖,卻漸漸穩下來。夜晚,他們坐在火堆旁,他會講些村裡的笑話,她偶爾扯扯嘴角,像在試著笑。她的夢裡還是會出現過去,阿爾弗雷德的低吼與士兵的笑聲像影子纏著她,可醒來時,艾倫的手總握著她的,粗糙而溫暖,讓她感到一絲安寧。日子平淡,像春風,緩緩撫平她的傷痕。
某夜,月光透進小屋,她看著熟睡的艾倫,臉上的輪廓硬朗卻溫柔。她伸手碰了碰他的手,第一次主動握住,心裡湧起一股陌生的暖流。她不知道這是不是新生,但至少,這一刻,她不再是那個地下室的囚徒。
ns3.135.190.188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