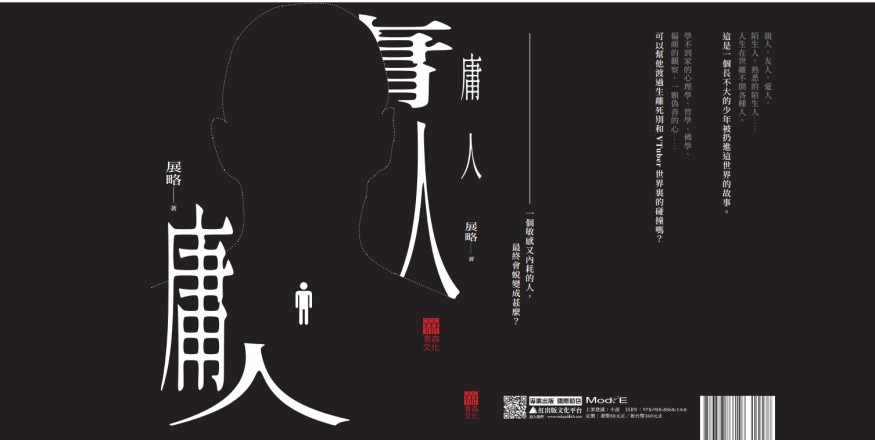「讓我看看你寫成甚麼樣?」
……
從地鐵站走出來,入商場上三樓,出到圓形小廣場就能放眼望見乒乓球檯。殷石楠從那裏經過,心想雖然這麼近,自己卻沒有來打過乒乓球。是他從來沒有主動來過,但反正來了也不會搶得到檯。雖然他不會打乒乓球,也不想嘗試,但不知為何總有一點空虛。可能是羨慕別人開心的樣子吧。視線從乒乓球檯離開,楠推開大廈門進去。
這裏是黃大仙一屋邨,殷家就住在這裏。
從家門就能看到沙發上躺著一個身形苗條,比例高挑,長髮馬尾,神情透露些許灑脫英氣的女子正舉著手機傳訊息。
楠的視線從鐵閘口穿過整個飯廳,看向窗台,再看到廁所門開著,基本就能肯定現在只有他和姐姐。楠進門一邊脫鞋一邊問:「爺爺呢?」
「買完自己吃的菜回來後又出去了……我也準備出門了。」姐姐說罷起身,一邊收拾袋裏物品一邊交代:「叫我買的菜我買好了。我不回來吃飯。飯煲已經少落了我那份。」
「又是這樣。她又要罵你了。」
「罵就罵吧。」
眼看姐姐快出門,楠在她臨走前問一句:「你既然要出街,剛才還躺著?不怕弄亂髮型嗎?」楠看著姐姐,她摸一摸頭,頭側向右方,右手順方向撥一撥長髮,說:「無所謂啦。去見男朋友。」
幾乎是聽到這句話的一瞬間,雖然表面看不出來,但楠有些不快。
姐姐走了。殷石楠也收拾收拾,拿出功課趕快做。
他今年中五,快將面對高壓的文憑試,課業繁重得即使自己一人在家,也沒別的心思做其他事。但是明知功課是較緊急,他偏要放一放――可能是因為不想面對壓力吧。他拿出書本,溫習令他煩惱的企會財內容。
他的選修科選了商科的企會財和經濟科,因為父母都可以教他。而以他的能力確實選其他科也不會有更好的結果,接受父母的幫助還可令他有那麼一絲機會考上大學。
一直到晚上,媽回來了,馬上準備做飯。她一邊問楠:「還有多少?」
「很多。」
「做了多少?」
「……」他遲疑後回答:「一篇作文。」
媽馬上說:「一篇作文你花那麼多時間做甚麼?夠字數就好了!」
「嗯……」
拿出其他功課,但一時間難以轉變思維,他看著功課嘆了一口氣。一是嘆自己能力太低,二是嘆學校沒有文學等科目作為選修課。
「怎麼個個都未回來?」
「對了,姐不回來吃飯。」
「那個殷紅櫻!」媽用力嘆了一口氣。
不久,爺爺哼著粵曲回來。隔一會兒爸爸也回來了,記得楠今天派考試成績,問了一句。媽媽邊做飯邊著急:「拿出來。」
楠拿出試卷,不出意外聽到媽說:「數學又不及格了?」
「我文科成續好……」
媽媽提高聲量:「你傻的嗎?人說東你說西。」
楠想解釋:「人人擅長的都不一樣……」
「不要找藉口!大家都是這樣讀書,我就沒有過不及格。」
爺爺幫口:「孩子會有自己的分寸,真的不行就轉個補習老師吧。」
媽媽說:「補這麼久都沒用,是他沒有開竅,不懂用腦!」
好不容易對話完了。飯也煮好。
吃飯時已是九點鐘,吃到一半姐姐也回家。媽媽馬上說:「我不喜歡你這樣。晚晚如是!」
「我喜歡的話不回來也行。」
「你有本事嗎?」
爺爺發聲:「用不著動氣啊。我都沒你們好氣。」
說完目光看回手機微笑。媽降下聲量對爺爺說:「連老爺都中手機毒。你眼睛不好啊,少看點。」
「OK、OK!」
爸爸問:「怎麼講英文了,肯定又跟霞姨通訊?明天就能見,現在談少一會兒也不行?」
吃過飯後爸爸在客廳看電視,媽媽回自己和姐姐共用的房間。爺爺拿張木製的小矮凳在露台念佛。
爺爺殷天賜是一個居士,投入佛教是從爸爸成年後,生活的重擔能稍為放鬆一點後的事。但是早從爸爸到了聽得懂教導的年紀開始,記憶中就有來自爺爺佛學智慧的灌輸,這對爸爸比較早懂事,可以負起責任,性格老實堅韌有很大的功勞。殷石楠兩姐弟也是,他們在小時候不只爸爸媽媽給他們灌輸價值觀,也受到過爺爺的教導。他們小時候都是很乖的孩子。
弟弟回房間,姐姐跟著進去。因為現在媽媽在房間,所以她過來這邊了。
可能是因為媽媽的強勢,不知從何時開始,姐姐和媽媽越來越對立。自從姐姐對人生看法多了,她們的矛盾就越來越多。到交了現在這個男朋友後,他們之間幾乎每次開口都是拌嘴了。
但這並沒有對殷家其他人造成困擾。這就是她們的相處方式。有時殷石楠甚至慶幸家裏還有兩個敢言的人,萬一有甚麼事需要人出面,選擇也更多。
「你買的是甚麼?」楠看著姐姐手裏的小盒子問。
「這是遮瑕膏。」
「有甚麼用?」
「眼下臥蠶又深又黑,粉飾一下。」姐姐這是在練習化妝,她當然不會化全套,只是試一試新買回來的商品。她看向書桌前的弟弟:「做你的功課吧。」
「唉……」楠突然提高音量叫道:「黐孖筋!欠交算了!」他也不怕媽媽聽到,反而他有點期待媽媽聽到後的反應。他也不知道他在期待甚麼,總之就是想知道別人的各種反應。
「你得也說得沒錯啊……阿媽的確是黐筋。」姐扮作若無其事地說。
「撲哧!哈哈哈哈……」兩人相顧,止不住笑。
姐姐說:「你看你的眉毛這麼粗,和爸爸一樣。仔細一看眉心還有幾條雜毛,我幫你拔掉吧?」
「不要。」
「來吧。不痛的。」作勢要過去拔他的眉毛。楠左右回避,一個大晃身躲到被窩裏笑著說:「不要搞我!」
「嘿嘿。那麼怕幹嘛?」他們這樣嘻嘻哈哈擾攘了很久。
爸爸回楠這間房準備睡覺,兩母女也乖乖一起睡覺,爺爺則打開客廳沙發床睡。到了早上各自出門。
爸爸殷偉冠身形壯碩,有個小肚子,是會計師樓的核數經理。處於這個職位是因為他做得久,可以檢查同事的工作。公司其他幾個經理也是順其自然升上來的。以他的資歷雖然比下有餘,在公司卻沒有上升空間了。他今天也跟平日一樣在「豬肉檯」――就是開放式辦公的大桌,對面圍住的一小格私人空間工作。這偽劣的「房間」分出了他和下屬的身份,也表現出他們之間的隔閡。雖是有自己的空間,但卻不比坐在「豬肉檯」舒服多少。「這『雞肋』的情況恰好與我在老闆心中的份量一樣,也算是適得其所吧。」這是爸爸自己的原話。
媽媽白明蕊生完小孩後稍有富貴相,看得出以前是美人胚子,也是個打工仔。在一家跨國公司的香港分部工作,是會計及人事經理。她在公司頤指氣使,今天上班也像打仗一般指點春秋。皆因在她工作部門中,她是資歷最深的那批人,多年來,也有不少變革是她的功勞。上司是上頭派下來的外國人,有很多問題反而要主動請她協助。儘管她的工作很多,有時甚至超出自己的工作範圍,但她卻往往可以不用加班,準時放工,這是她最厲害的地方。可能要回家煮飯的壓力也是工作快的一個因素,還因為她培養了一群優秀的手下幫她收拾工作。
姐姐現在身處哪裏,那就比較難知道。她以前有一份全職工作,後來覺得不適合自己就沒做了,現在主要「炒散」。現在吃飯時間,多半在某一個商場裏吧。
午飯時間,殷石楠在學校正門的接待處拿到爺爺剛送過來的飯菜。這做法從中一開始直到現在。
入廁所時遇到同學同樣進去,問:「去食飯?」對方沒有搭話。楠入廁格邊反省:「怎麼會看著人入廁所問是不是去食飯?」待外面沒有聲響他才出來,邊洗手邊抬頭望鏡說:「傻仔。」
吃完飯回到課室上課,又是不須發一言,捱到放學,便馬上回家。
與投入打球、玩桌遊的同學不同,他會留在學校唯一的原因就是學會活動,但身為公益少年團成員的他,一年也不須參與幾次學會活動,自然每天早回家。
「也好。老師給了這麼多功課,趕快做完趕快睡。」殷石楠作為少數「歸宅部」成員,抱著這想法。不管其他人本來是怎麼想他這種人,如果他們知道殷石楠回家後真的是實行自己的學習計劃,也會多了一點點尊重吧。不過他做功課的速度慢,又沒有玩到,又沒有早睡,成績也沒有好到哪裏,那一點點的尊重又會消失吧?
殷石楠回到家門口,準備開門,心裏想著趕快做功課。還未開門,他就看到與昨天不一樣,明明不是吃飯時間,飯桌卻早就搬來展開在沙發前。飯桌上放著熱茶,是為了客人而斟,只因殷家沒有茶几,拿飯桌來充當,反正只要不擋電視,沒有甚麼所謂。坐在沙發的是爺爺和霞姨,他們正邊看電視邊吃花生,看這樣子,霞姨應該來了很久。姐姐也已經回家了,因為平時攤睡玩手機的位置被坐了,拿了張椅子圍住飯桌,坐在爺爺的左面,左手伸出放在桌上,身子彎下去,頭睡在自己的左臂,右手按手機,絲毫沒有把霞姨當客人的感覺。因為姐姐正對門口,這副模樣殷石楠在門口進來前就看見了。
他知道要做好心理準備,即將面對一輪寒暄。
「楠仔,放學了?」
「嗯……我有很多功課,我先做功課了。」
「啊。」
寒暄的時間比殷石楠想像中短。也許是因為見過太多次,霞姨覺得彼此已經熟到沒有必要沒話找話說吧。確實,殷家人都已很了解霞姨,但了解殷石楠這件事,卻只是霞姨自以為而已。
楠向著桌子坐在霞姨的右邊。雖然他肯定是更願意坐在姐姐或爺爺的旁邊,但為了不阻到人看電視,他似乎也沒有選擇。
其實楠心裏並不是不喜歡霞姨的。在她身邊也還算自在,反而因為霞姨偶爾會轉過頭來看看他做功課,給到他一種監察的感覺,效率還有所提高。但做得再快,遇到無法解決的問題,也總要停下來。
「唉……為甚麼……到底為甚麼?」殷石楠卡在了一條數學題上。想來想去想不出從何入手,漸漸心情煩躁起來。他嚷出:「讀這麼多這麼深的數學做甚麼?誰可以靠三角函數改變命運……有!希帕索斯。他用畢氏定理研究太多,被人丟進海裏浸Q死了!」
眾人沉默。姐用小聲但足以所有人聽到的聲量說:「別人學計算,你只顧著聽故事,難怪學不會……」
「啊――」楠仰天大叫,姐失聲大笑,長輩們也被這對活寶逗笑了。只是,殷石楠並不是在搞笑。
後來姐姐嘗試用所剩無幾的記憶,提一提做題目要注意甚麼,但是實質的幫助為零,只令殷石楠更煩躁。
爸媽都回來後,觀察到他的眉頭眼額,問他怎麼了。
楠並沒有理他們,只是自顧自搖頭嘆氣。他是覺得很煩,功課很煩、生活很煩、爸媽很煩。
爸爸媽媽只是關心他,他這種反應看似不妥,但是其實是有原因的。
他是一個不喜歡表達自己的人。喜歡獨處沒有問題,喜歡聯繫沒有問題,兩種不同的人非要處於一個親密距離就出現了問題。爸媽這種方式的關心只會令他感到很煩。其實以前也不是這樣的,只是現在楠有了新的――或者說正常的角度去看:爸媽跟本從來沒做好過聆聽者的角色。
以前分享學校趣事和荒謬事,得到反應是:「那當然會變成這樣。」或「你們就自己搞得不好……」
分享社團活動拿了好成績,他們第一反應是:「有獎嗎?」說有罕見的天文現象,得到的感想是:「那對我又沒有影響。」
有情緒和脾氣,他們的回應是:「不開心有甚麼用?」或「發脾氣代表甚麼?只代表你無能。」
現在,他們覺得楠應該把心事說出來,在楠的角度簡直莫名其妙。
「你們根本不在意我想甚麼……不過也對,為甚麼要在意其他人想甚麼?」這個想法種在了他的心裏。楠不是「不分享就會死星人」,交流的需求不被滿足,那放棄這種需求就好了――他是向這種方向努力的。
「你有甚麼事情就說出來吧。」媽堅持,而爸也一副很關注他怎麼了的樣子。
就算他不願,也只好說點甚麼吧。他兩手胡亂地拿起一些功課,然後用那些功課指著另一堆功課,說出:「我這些、這些,還有這些……很煩……」
媽媽說:「人就是要做討厭的事情,只做喜歡的事情是不足以生存下去的。你討厭又怎樣?解決問題最重要。」
「唉……」果然,他是不應該開口的。有時他會想,要是自己口才好一點,可以好好表達的話,也不至於引來這麼無情的說教。
爸說:「你媽說得對。」楠答:「正論不是問題,但為甚麼要Punch……」他越說聲音越小。
「甚麼意思?」
「沒有。」他現在只想這間屋再沒有人說話。
「你們不會明白的……各種意義上……」他自己靜靜地想。
功課都做好了,開飯時間,霞姨邊吃邊問楠怎麼還是面如死灰的樣子。楠本想甚麼也不說,然後想到這可能是一個嘗試表達自己的機會,但是他又不敢正面回答為甚麼他不高興,於是他就迂迴曲折地說:「以前我跟你們說手冊留了在課室,做不了功課的那件事,那時候你們的反應還記得嗎?」
媽第一個作反應:「甚麼啊……啊。很久以前了……那時你念小學吧?這樣還記得?你也太小氣(粵=心量小)了吧。」
「小氣?」楠微微低頭看著自己那碗飯,嘀咕著:「是啊……這詞……」他是真的忘記了還有「小氣」這個詞。其實他忘記了很多其他人會拿來評價別人的用詞,因為他不評價別人,也不想被別人評價,這些用詞對他來說是這麼陌生。現在他正是在想自己是不是符合「小氣」這個詞。
「那跟你現在不高興有甚麼關係?你就是因為以前那件事不高興到現在嗎?」爸單純地疑惑。但是爸不知道這句說話在殷石楠聽起來是要他在「沒有邏輯」和「小氣」當中二擇其一。對現在脆弱的他來說,多想一秒這個問題,就像是被仙人掌扎到一樣刺痛。
他們見楠不再說下去,默默地繼續吃飯。
晚飯過後兩姐弟在房間各自做自己的事情,連霞姨甚麼時候走的也不知道。不過其實姐姐只是坐在楠的床上隨意在手機上看新聞,而殷石楠根本甚麼也沒做,只是坐在書桌前放空。
「你到底怎麼了?很憂鬱嗎?有甚麼事情?」楠聽完姐姐的提問後並沒有打算馬上回答,雙眼依然放空地望著書桌上方吊櫃放著的模型。
「人死了起碼有七七四十九日清靜。」他說。不知為何他現在最想說的就是這一句,而他在姐姐旁邊能放鬆地說出來。
姐不再看手機,半認真地說:「如果根據這套的話,那自殺可是要下地獄的喔。」
姐姐起來,站到弟弟旁邊摟著他,說:「傻仔,失敗就失敗,最壞頂多留在家中啃老。」
「你說到好像他們一定願意一樣……」楠說。
「如果是你的話,他們願意的,他們還是很疼你的。」
「……」
「提起精神吧。家裏有足夠多大學生了,不一定要再多一個。」
楠本能地想澄清自己:「我只是想……」
他停住了,接下來沒有字在他的腦海中浮現,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我想上大學……」
「你既然想,就撐住吧,不要說個『死』字。」
「嗯……」
楠覺得這個狀況「萬一」被「外界」看到,他會不自在,雖然不情願,還是輕輕甩開姐姐,轉身去躺在床上。姐接著坐在床邊對他說:「我不能一直陪著你,要學會堅強,知道不?」「嗯……」
殷石楠只能答應。這時候,他還不相信,有些問題,是不一定要根據別人的希望來回答的。
另一邊,爸爸也在媽媽的房間與她交談。
「兒子跟你一模一樣!」要是旁人就會覺得媽媽的語氣是生氣,但爸爸能聽出這只是不知怎麼辦,再加半點無奈之下的反應,媽媽的語氣從來都是這麼容易讓人誤解的。
「女兒就不知是似誰,至少感情方面肯定是似老爺!」
爸爸點一點頭應答:「也沒甚麼不好,他們沒有學壞,也不似會學壞,已經很好,紅纓喜歡的話就隨她吧,反正我們家的人在感情方面都是這樣。」
沒錯。媽媽說姐姐感情方面像爺爺不無道理,而且在說的不是過去的爺爺,而是現在。
爺爺再婚了,現在的妻子正是霞姨。
當初爺爺宣布要和一個叫銀金霞的女人結婚時,眾人是十分的困惑。老人家找個另一半相依為命,這種事並不罕見。但是像爺爺每天有事做作消遣,又有子孫陪伴在身邊,還要找一個伴的話,在殷家其他人的角度,實在想不透。而且也沒有名正言順結婚的必要。當時就只有姐姐殷紅櫻第一時間表示了支持。
爸爸沒馬上贊成,倒是跟他對親生母親的情結無關。殷偉冠的媽媽早過世,他是由父親養大的。
爺爺是一個溫柔而堅強的人,他的軟心腸令他難以擔任嚴父的角色,然而即使再溫柔也跟慈母的愛有一點不一樣。儘管艱難,他儘量給爸爸雙份,甚至更多的愛。無庸置疑,殷偉冠幸福地長大了。他懂事,從來沒令父親為難,對父親的尊重和關懷大家都看在眼裏。
當時家裏只有他們,倆父子的起居飲食相當隨便,兩人的默契和性格令他們話也不用多說一句。家裏無風無浪,有的只是日用品,枯燥得難以想像,直到爸爸把媽媽帶回來。
當年要娶白明蕊過門前,她已願意為殷家打點、處事、做家務。殷家爺倆可是久遺地有被照顧的感覺,如沐春風。在他人看來,當時媽媽可能算是「蝕」了給男人的蠢女人,但如果非要用輸贏的角度來看,那放眼現在,最大的贏家可能是媽媽。總之,爺爺認定媽媽是對殷家來說最好的媳婦,爸爸認定娶到媽媽是自己的福氣,不論任何時候都這樣認為。小時候很少被管的殷偉冠,下半生再怎麼被老婆管,也是心甘情願。
當時在討論爺爺再婚這件事的時候,就是在家裏如此有話語權的媽媽,毫不保留地表達過大家都存有的那一絲猜疑:霞姨是想騙爺爺的棺材本。但爺爺極力撇除這個可能,銀金霞不是這樣的人。對家庭關心到接近是控制狂的媽媽,也只好接受,只要爺爺願意,就讓她騙也沒關係,反正有殷家這麼多人,爺爺也不會一無所有。
爸爸後來也轉為支持爺爺的決定。轉變的原因是非常戲劇性的,就是因為他看到爺爺為霞姨抹汗的一幕,想起自己小時候,父親也這樣為自己抹汗。說出來可能十分搞笑,但就是這樣微小而真實的瞬間,令爸爸覺得,這可能是爺爺真心想做的事。
當然支持也好,猜忌也罷,爺爺怎樣都要和銀金霞結婚。也確實這樣做了。
現在霞姨一星期有幾天來殷家――也不知是算作客還是回家,吃完晚飯就走。爺爺也有幾天會到霞姨家過夜。
他們想過,把霞姨接過來住是不現實的。如果要爺爺到霞姨家長住,撇除要改變現在的生活方式這回事,大家還是不放心,所以否決了。當然爺爺的角度是不放心霞姨一個人,但其他人當然是更關心爺爺,而且霞姨也慣了一個人住。因此變成了現在這個奇特的模式。
「這到底是不是好事是很講運氣的!」媽媽對爸爸說。
殷家的門都沒關上的,其實稍為大聲一點就全屋都能聽到。
姐姐剛好要回房間拿東西,正預期父母看見她出現會把聲量收細,卻把剛才的對話都聽見了,她也大大方方正面應對。
「又說我甚麼了?」她進來一邊找東西一邊扮作不以為然地問。媽說:「說你真學足你爺爺。」
「對啊,反對再多也擋不住真愛的。」
媽媽閉上了嘴。儘管幾乎每次關於姐姐拍拖的「討論」都源於媽媽先開的口,但很多時,媽媽都是先閉上嘴的那個人。那不是因為無法反駁,而是在她內心,也希望女兒真的沒有錯。
其實媽媽並不是反對,只是因為某一天,殷紅櫻說現在這個男朋友是她在中學時已經交了的,一直到現在才坦白這件事。
對於「隱瞞」,她們辯了很多次,姐姐總是搬出媽媽的其中一句格言:「過去了就過去了,追究也沒用。」但姐姐從來不會真正擺脫。一件令人出乎意料的事就會改變一個人的形象。自此之後他們就算是小事都可以演變成爭論,也是離不開這個因。
這晚之後,日子過去不久,姐姐宣布她已經計劃好搬出去住,和男朋友同居。家人不情願,但也無法反對,加上姐姐舉了一堆例子說這很正常。媽媽也只盤著手,沒有任何表示。
就這樣默默到了殷紅櫻走的一天。這是一個星期日,就是家裏人齊聚的時候,她要拿著行李離開。
楠在姐姐的房間。本來也沒甚麼情緒,但一打算開口說話就有些哽咽,他努力壓抑住。但既然情緒都出來了,就不如說出真心話,他垂下頭低語:「我不捨得你……」
姐姐平常那水晶般閃著的眼神微微半閉,那是楠懷念的溫柔,她說:「沒甚麼好不捨得的,雖然我也有一樣的感覺,很奇怪對吧?明明不是再也見不到。」
楠對她說了句:「自己小心了。」然後姐姐出了房門,也準備走出家門。
除了行李的拉鍊聲和輪子拖動的聲音外,寂靜的氣氛被打破的第一句,來自爺爺的關心:「沒拿完的東西,再慢慢回來拿也可以。」
「都拿好了爺爺,我走了。」
爸爸心裏其實有一萬個不願意,真的這麼想離開我們?但這始終是她的選擇,而且所有提問她都一一回答好,還有甚麼好說?眼見女兒離踏出家門只有幾步之遙,他很想開口,但沒有道理可說,也不擅長打動人,沒有甚麼選擇下,爸說了一句:「女兒,我只是想你記住我們都……」躊躇了一瞬間,選擇說出口的是:「……真的關心你,記得常回來。」
姐知道爸爸想說甚麼,微微回頭對爸說:「你愛我是因為我是你女兒,但他愛我是因為我是殷紅櫻。」
「有分別嗎?」
「……我會回來的。」
爸知道女兒去意已決,她有自己必須追求的答案。當初她的媽也是不顧家人反對,嫁給一無所有的自己。
姐姐走了。爺爺獨自慨歎:「沒見過那個男人幾面,就要送個孫女去……」
媽媽終於說話:「又不是真的送了給別人……」
晚上,爸爸搬回來跟媽媽同房。兩人睡前,爸爸就知道媽媽有話說。他從來不擔心媽媽會有鬱結,但現在媽媽的表情是他未見過的。
「你說我怎麼不擔心?」媽媽少有地無神無氣說。
「那你剛才不說?」
「唉……她都決定了,當給她一點支持吧,不然又和我鬥嘴鬥到僵了。」爸爸總算看出來了,那表情更多的是失落。
櫻的男朋友叫沐一亭,比櫻高半個頭,比楠高更多。因為瘦削而顯得輪廓深邃,面型比例均勻,確實有幾分帥氣。髮型、穿著、神情……看起來就是一股「年輕的感覺」。
他跟父母關係不太好。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三,兩位兄長都是專業人士,妹妹快將畢業,準備做老師。其他人養家就可以,他想做甚麼基本上沒人管――甚至沒人關心,而他似乎也不需要其他人管的樣子。
他是間小公司的小股東。說是有股權,但都是老闆以廉價工資綁住員工的手段。當初說得好像只有被看得起的有能之士,才會得到入股邀請,他可能是為了老闆夢,也可能是為了當另類晉升,而投入了資本,順帶押上了自己的前途。在商場打滾多年的冠和蕊懂得這些,因此沒特別想交託女兒給他。不過不反對他們拍拖。只是內心期望他們拍拍拖就好了。
沐一亭曾經來過家裏,他只和殷石楠見過一次面,就留下了非常不好的主觀印象。
殷石楠對他的評價是一個說話輕佻,又喜歡大談自己的想法,總給別人挑刺和調侃,明顯重視口頭上佔便宜的人。有時裝神弄鬼,陰陽怪氣,要引人注意。
在殷石楠眼中,這個人成熟的面孔背後,根本還是一個「小學雞」。只不過聰明了一點,做得更好罷了。他總能成功引起人注意,那是當然的,畢竟,他除此之外一無是處。
他稍為算得上有點「小聰明」的地方,就是令人在意他,再用嘲弄、挖苦,樹立聰明的形象,並令人越來越想得到他的認同,惡作劇令人期待下一次他會做甚麼,配合適當時機表達喜歡和內心的脆弱,令人被他吊住。殷石楠甚至能見到PUA的影子,只是未到「一啖砂糖一啖屎」這麼強而已。在殷石楠眼中,姐姐就是被他用這種小把戲迷住的。
殷石楠細想,可能都是因為人家父母沒有給他足夠的關心,才習慣用這種方式生存,然後發覺這樣莫名其妙有助泡妞。他把姐姐泡到手,真的應該恭喜他。更應該恭喜他的,是他這一生到目前為止還未遇到一個人,去揭露他脆弱的內心,把他蹂躪得體無完膚。畢竟他的弱點實在太明顯了。
殷石楠也承認自己的想法是有點惡毒――他經常覺得自己惡毒,不知他這樣算不算善良。不過反正他不會把想法說出口。很多時他沉默不語,是因為他的想法太邪惡,怕傷到人,更怕之後傷到自己。
雖然不會說出口,其實也不是想像這麼小事。很多時,這些惡毒的想法出現後,自己反而更無法釋懷了。因為已經把別人和這個世界都定型了。把他放到心中的那個「敵人」的位置後,就可以任由那種討厭,肆無忌憚地成長和攻擊,那種難受就更難消淡了。
不過就算再怎樣,楠也不會與他對立,只不過楠覺得佷「無聊」罷了――不只是對於他這個人,想到他們在交往,還有跟他相關的一切,尤其是當人因為他的玩笑而嘻嘻哈哈,就「無聊」到受不了。楠分辨自己感受的能力在這時還不夠,他只懂當作是「無聊」就完事了。
他不滿姐姐被人用他不喜歡,甚至不屑的方式帶走,至於到底是本身對「某種人」反感,還是因為姐姐被這樣帶走了,所以對「某種人」反感,他還不知道。可能兩樣都有吧?
他不知道的,還有姐姐明明是如此有思想、有主見的人,為甚麼會喜歡這個「小學雞」。
大概過了一個月。某平日,櫻接到電話,說要她晚上去醫院。這通電話本應下午就打出,但是那時候尚未到探病時間,無謂要人白白多擔心幾個小時。
這間醫院她非常熟,弟弟從小在這裏看兒科、耳鼻喉科和骨科。楠小時候經常肩膀脫臼,在這裏檢查和覆診過許多次,有時是姐姐陪他來的。但這次再到骨科,卻是因為不同原因而要上病房。
上到病房看見爸媽都在,他們是放工後來的,早那麼一點點。姐姐拿出了牙刷、毛巾、拖鞋等日用品,那是早就在電話溝通好,要她回黃大仙的家一趟再帶過來的。
媽媽摸著剛打好的石膏問:「痛不痛?」
楠回答:「吃了止痛藥,不痛。」
媽媽再問:「怎麼從山崖掉下來了?你分了心嗎?」
「嗯……」楠撇開眼神不敢看人。
殷石楠是在學校旅行途中,自由活動時失足跌傷了,順勢側身落地時,手臂撞石頭骨折了,腿腳事情不大,但也足夠行動不便一段日子。
當時媽媽接到電話,應該有點被嚇到,不過那是楠受傷後親自打的電話,他在電話平平淡淡地說自己受傷,要上救護車,經媽媽轉述後,可能他們比起擔心和不停想像壞情況,佔據腦海更多的是:「啊……又有事發生了!」的想法吧。
「對不起。」
「你舒服一點了?」媽媽問楠。
「嗯。對不起。」
「傻仔。有甚麼好對不起,你做甚麼也不會辜負我們。」媽媽望向櫻,說:「家姐也是。」想來這時候,她應該是借著機會說這句的,而比起盲目地詢問楠的狀況,這一句確實更為重要。
殷石楠眼淚已流下來。大家都受感染,殷紅櫻也是。
「因為我們的女兒是殷紅櫻,我們的兒子是殷石楠。」這是來自爸爸的一句,是給姐姐的一句。
這句話很單純,但也許就是應該如此單純。
過後姐姐主動說要搬回來,說是幫忙照顧弟弟。不知道這是不是唯一的原因,總之他們又在一起了。對楠來說不算一件「好事」――只是終於回復正常。
可能那一晚真的在大家心裏留下了甚麼,加上生活上,大家都變成了照顧者,所有人都溫和了。為了照顧殷石楠,姐姐和爺爺共同協作的機會多了,媽媽反而光說做法,不太動手,但是動手的人和指點的人不再有矛盾。
在此期間,殷石楠不知道是否感悟力太強,他悟出了一個想法:也許應該謙卑地承認,有些問題最好的處理,就是不處理,只能祈求當其再次觸動我們神經時,我們有新的力量去面對。
而他為了這份力量不斷準備著自己內心。
但不管人準備好,還是未準備好,姐姐還是宣佈懷孕了。沐一亭也正式求了婚,打算在姐姐身材未變之前結婚。
令人安慰的是,亭認真承諾殷家,不是像女兒被拐帶走,少了個家人,而是多了他一個家人。那堅決有擔當的模樣,有點出乎人意料,反正所有人都認可了這是一件大喜事。
除了慶幸和祝賀之外,也沒有甚麼其他想法了――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那是一個高興、熱鬧的婚禮。燈光打在眾人中間,姐姐一步一步走向台上。有人說這一刻的女人是最美的,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幸福的眼淚和笑容肯定是最閃閃發光的。
賓客台下祝福今後滿滿愛意,新人台上感激過往處處親恩。從此姐姐就是沐家人了,不過她同時也永遠是殷家人。
姐姐婚後搬走了。霞姨住到殷家,算是終於有點跟霞姨是一家人的樣子。
之後女兒出世,取名沐茵薇。
ns18.117.75.226da2